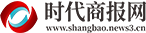《种子与播种者》原著全文翻译【第9期】
X 关闭
枫言枫语: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自从开始搞翻译,不知不觉中,我开始留心生活中见到的各种英语。看到任何生词,都会本能地记下来去查它的意思。前几天去看了《第二性》的小剧场话剧,在奥尔格伦把波伏娃写给他的一盒情书向观众席扬去时,我期待信封里是有内容的。果不其然,每个信封里都装着情书!英文的!经得允许,我们一行三人各拿走了一封情书,以做留念。
既有缘又有趣的是,我发现我与文中翻译的人物有着极大相似的情感经验(我想等正文全部翻译完,讲讲我的故事),这有助于我了解他们,也有助于我审查自己的内心。有时候,越翻译越感到沉重、气闷,越想站在瓢泼大雨中看《罪与罚》。
面对背叛,我们总觉得自己是苦大仇深的侍萍,别人是刻薄冷漠的周朴园,都想做轰轰烈烈的蘩漪。可面对现实时,大多数人是软弱逃避的周萍。
你曾被背叛过吗?
你曾背叛过别人吗?
---------------------------------------正文分界线------------------------------------ 第二章 圣诞之晨:种子与播种者
第一节清晨之后
在约翰·劳伦斯和我讲关于原的事之后,便是圣诞节的早晨。我起得很早,发现自己心不在焉,还沉迷在杰克·塞里阿兹的回忆中。我在天光乍破,甚至是我的两个孩子睡醒前,就悄摸起床下楼去书房了。我打开桌子上一个放着我最重要东西的隔层的锁,取出了七个纸板文件夹。
我迅速打开了最上面的一个,确定里面的内容完好无损。看到塞里阿兹用肌肉紧绷的手写在几张粗糙的黄色厕纸上的字(厕纸是日本人允许我们在监狱里使用的唯一一种纸),我便打消了不安。
虽然那张薄纸的边缘有磨损,而且由于牢房石头地板的潮湿已经有局部的腐烂(当时,它被裹在一张破烂的军用防潮布里)但那字迹却格外清晰,好像它不过是刚刚写好的事件描述,而非已有八年之久。只一会儿功夫,我拿的这块薄纸就让我的手掌和手指感到刺痛,仿佛对这个奇迹表示震惊似的。这个奇迹使它不仅在爪哇黑暗潮湿的土地上保留下来,还在逮捕我们的人的疯狂搜查中得以幸存。最终,战争结束的多年之后,爪哇的平民石匠会发现它。他甚至可能会很震惊地把它交给一个军官,而这个军官碰巧认识我。当这个男人看见外面写着我在英国的名字和地址,并读了这番应该是递送给我的恳求时,他忽略正式的手续,立刻把信寄给了我。这么做,对他自己是有风险的。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再次陷入沉思,就像自从我收到它后常常会做的那样。这真是奇怪啊,塞里阿兹竟会选我做他的收件人。在他那边儿一定有很多人比他知道的更多。其实,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不把信寄给他在叙述中令他如此苦恼的弟弟。但是,当我自己去到他的故居,我发现这也没什么用。然而,由于他的一个暗示清楚地预见了将要发生的事,这就使他的行为更显奇怪。
但是,或许对我来说最奇怪的,是当我坐在寂静的圣诞节的清晨时,它竟然安然无恙地在我手中,正准备拿给约翰·劳伦斯看。在前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关于他自己和原的事,这使我感觉塞里阿兹可能会写一个不是给他自己,不是给我,甚至不是给他的弟弟,而一定是给劳伦斯的文件。我几乎不能等待早晨的到来,我离开了兴奋的孩子们,走出教堂。早饭后我立刻把劳伦斯拉到一边问:“你记得杰克·塞里阿兹吗?”
他看起来很是迷惑,我赶紧补充到:“你肯定知道!就是我第一次在北非后方突袭,后来又和第51突击队在西部沙漠的那个高大帅气的南非军官?他有时候会和我在食堂里一起吃饭。”
“天哪!”劳伦斯惊呼一声,他的灰眼睛因为感兴趣而快速地转动着:“我当然记得他,他是一个非凡的战士。除此之外,他几乎是我见过的所有男人中,唯一一个可以称其为美丽的人。我现在就能看到他……他在漫步……他看起来几乎像一个动物,总是踮起脚尖,放松脚踝。他有着狮子样的勇敢,骆驼般的忍耐!你说的就是这个人,对吧?他不是有什么外号吗……?
我点头说:“那就是塞里阿兹,士兵们都叫他‘扫射杰克’。我给塞里阿兹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在1941年危险的利比亚前线时很有名气。”
“你知道吗”劳伦斯接着说:“近来我常常想起他的很多事。就在昨天,我还在想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不可能还活着。我从来不像你那么了解他。当然,你也知道他从不会多说话,最起码不会对我说那么多。当我记得他是一个古怪沉默的人时,他却又能够聊的很好……”他停顿了一下。“但是,在我看来,他有时的表现好像是想去送命一样”。
“或许,你的感觉并没有太大问题。”我平静地说。
“那么,他是自杀了吗?他怎么了?为什么你现在问我还记不记得得他?”劳伦斯飞快地提问,他的想象力显然被激起了。
我说:“听我说!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希望你能先读读他之前写的文件。我们昨夜聊的那些让我感到你应该是它的保管人,而不是我。读读它,这不会用太多时间,然后我们就能聊聊了。”
我让劳伦斯独自坐着,他低着头读那张黄色的纸。时间以亲密的姿态在他精巧的头和反应迅速的脸上写下了自己的意义。劳伦斯身后,圣诞节里柔和的灰色调的天空出现在大地的上方。在监狱中,这样的场景一直如人间天堂般萦绕在我的脑际。
接下来这些内容,就是劳伦斯所读到的。
第二节 弟弟
当我有弟弟时,我就背叛了他。
背叛本身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大多数人会觉得“背叛”一词太夸张了,他们觉得我对这个字眼有着病态的敏感。然而,正如一个人从树的种子中认识到它的本质,从果实中认识到树的本质,从舌头的品尝中认识到果实的本质一样。我认识背叛,正是从它的后果和其遗留在我情感中的暴虐。
这是背叛最基本的一点,毫无疑问,最好在开头就把它写下来。虽然我说这无需骄傲或谦卑,只是作为我生活中的事实,我现在就是作为这个问题的专家说的。同样,我可以向你保证,背叛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起源既不令人惊叹也不会感到冒昧。事实上,那些注定要造成最严重后果的背叛,一开始并不会表现得过于明显或满是戏剧性,而是会谦卑低调地等待着,直到成熟时准备好承受苦果。它们似乎喜欢把自己呈现给没有戒备的心(这些人被选中成为它私人的种子温床),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微不足道的存在一样显而易见。以至于它们出现在日常事件熟悉的场景中,不会有选择上的困难和拒绝的机会。事实上,背叛之举的价值好像不会超过那少得可怜的不义之财。而这,也正是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意义的背叛。
我认为,这不仅是它最基础的,而且是最可怕的方面之一。例如,将背叛与另一种在渺小中成为伟大的东西,也就是忠诚进行对比。不管人的意识对忠诚的追求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远到生命的尽头,忠诚也依旧站在这个世界的门口。只要心有所依,忠诚便可移山填海。但是背叛的存在却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东西。它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拒绝,一个随意的否定开始,就像现实中不存在的致命龙葵的虚幻花粉。
仿佛和欧几里得直觉中心的几何点一样,背叛的存在无需大小,而是只需一个位置。就在此时此地的这个环境,我想讲讲,我自己生命中的背叛在哪个位置。
我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接着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但是,我的两个妹妹都死于流行伤寒。这种病在偏远的非洲世界肆虐横行,就像埃及的瘟疫一样,发生在每一次严重的干旱之前。所以,我弟弟和我离开了那儿。某天,母亲压抑着情绪说,我当时太小,不能忍受我的宠爱不仅被弟弟,而且被两个妹妹给分走。我在此旧事重提,并非我迟迟才了解她的感受。而是因为多年以后,我有理由记住这段话。
我和我弟弟差了七岁,而这七年也有了它们自己的差距,因为它们身上柔嫩的血肉被残忍地榨取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的变化是贫乏且饥馑的。就像挨饿的人在时间的河床中迈着缓慢的行巫似的步伐,就像法老梦中瘦弱的牧群,警告着约瑟夫巨大的饥荒将要来临。因此,这就给我弟弟和我的年龄差之间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压力,对生死均有影响。
然而,这仅仅是我们之间众多差别中的一个。还有很多我不得不提,因为它们有助于讲我的故事。
首先,我天生白皙,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我被生得很好,长得又高又壮。我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和阻碍,能攻击我在言行举止间流露出的对自己外貌的自信。在我们周遭这个广阔的自然世界里,我感到很自在。与身处其中的人们交往时,我也很放松。
我似乎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就像一尾在琥珀色的海洋里款款游过的金鱼。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和最优秀的同龄人一起玩耍、骑马、射击、干活。当倨傲狡猾,经验丰富的古老的非洲大地,嘲弄并激怒了它所孕育的生命时,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告诉自己,我不知疲倦且毫无惧色。我说话很得体,长得也很好。
其实,最后这句话对我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却太轻描淡写了,我真应该展开聊聊。
事实上,从我很小的时候起,许多人就发现我长相惊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深深地被我的外表所吸引。这也是我再次重复的一件事,我并不感到骄傲或谦虚,也没有自负或洋洋得意。我早已到达内心骚动的菱形点,只有事实,唯有事实,准确地观察和认真的解释,方可打动我。
我知道,唯有事实才能拯救我。我热切地期盼着能从我存在的事实中锻造一个足够强大的武器,使我能反击我和我的时代精神傲慢推进的虚权与浮华。但是对于我的外貌来讲,如果说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别的情绪的话,那就是一种微妙而普遍的厌恶。
或许,这听起来是对给予我如此偏爱的生活的忘恩负义?然而,真相依然存在。我的一部分人格对我的外表愤愤不平,并把我的下场归罪于它们。
我有一个生下来就是侏儒的邻居,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每当我看见他,我都会同情他,并为自己没有被赋予他那样身材而感激不尽。但时至今日,我不确定我该不该嫉妒他。我只是不知道,哪一种对身心的完整构成最大的危险:是吸引还是排斥,是招致厌恶还是令人喜欢。毕竟,那个侏儒,仅仅赢得了怜悯和害怕。而人们哪怕是这样做,也并不过分。但是他们对我的敌人立刻产生了磁力般的好感,在我不知道身处何方,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之前,我就成了一名对他们施以影响的犯人。
这个侏儒被他的畸形死死地束缚住了。但是,与其说束缚住我的是俊美的外表,不如说是人们在看到我之后萌生的最初幻想。然后,他们会通过想象强迫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知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周围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诱使我离开了本心,把我从内心存在的焦点中拉了出来,使我头也不回地转入到我的仰慕者和他们在令人费解的定律中磁吸铁般地为我着迷,所下意识地要求我扮演的角色中去。直到现在,我在回忆起其他人对我的强迫,是像对机械装置的操控和效率一样毫无人情味儿,就感到不寒而栗。它迫使我把那小小的不可替代的血肉之躯,奉献给我周围幽暗的欲念、虚幻的愿望和没有生命的自我。
但可以肯定,我慢慢地长成了一个痛苦地疏远了自己本性的人:我如同一个在远方饥肠辘辘的浪子,没有任何梦想可以打动我漂泊的肉体。可以说,我受到了海伦的诅咒,她的脸“使无数船只沉没,使高耸入云的巨塔焚毁”。海伦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人们眼帘,长久以来,她像一个囚徒一样呆在那里。
我并没有因为任何百合花的倒影而有纳西索斯的自恋情结。我从不觉得自己长得好看。我时常在镜子和橱窗前驻足凝望,但我并非感到骄傲,只是偷偷摸摸地,好像我害怕看见镜子里的倒影是我感觉自己将要成为的样子。尽管有很多相反且可信的客观证据,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丑陋的人。我知道,别人觉得非常吸引人的东西,不过是某种更伟大的东西的外表,而它,和其他丑恶平等且无可挽回地联结在一起。
我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感觉到,我们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双胞胎。一对连体人总是每晚坐在我的圆桌旁呷着酒,这哥俩被设计成相互滋养和扶持的样子,但也莫名其妙地疏远并不断否定对方。
是的,尽管有种种挑衅,我永远不会像别人看我的眼光那样看待自己。
那个已经成为我主宰的倒影,并非在现代的镜子下银光闪闪,但又影影绰绰。而是像黑灌木丛里的一方池塘,光滑如镜的表面下缓缓地闪烁着微光,像黑人手里的结婚戒指一样。
哦,我是如此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下马在闪着金光的水塘边解渴时,那方池塘和那个遥远的黎明。我跪在地上,右手鞠了一捧倒映着光的水,左手牵着我身边蒸汽银色马的缰绳。在喝水前,彩虹般的烟雾穿过波光粼粼的水面,马小心地吹了吹晨曦里的春季花粉。突然,在玫瑰红色的栅栏外,我那匹挑剔的马的嘴里发出了有节奏的震动。我看到我的倒影从紫色的池塘深处冒出来和我碰面。那倒影模模糊糊的,和我在这明媚的早晨对着水面弯腰俯身的样子截然不同。它停留在那里,这个黑暗的无甚光彩的影子,在轻轻波动被朝霞染红的春水间徒劳地挣扎着。仿佛潋滟的水面不是大自然微微颤抖的栅栏,而是一个人为设计的,永远囚禁它的笼子。
当时我感到悲伤。或许,要是它使我生气的话,可能会好一些。谁能懂这种感觉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但是,话又说回我弟弟和我之间的差异。他长得和我全然不像。他非常黑,超出了可以预测的遗传规律,好像父系和母系的基因在生他的时候都被控制住了。他的头发和我一样又浓又黑,这点倒是公平公正的。他的皮肤像地中海的橄榄树一样,而他的眼睛是他最好看的地方,它们很大,散发着黑灿灿的光芒。我每次看到它们都会感到心烦和难受,我希望我能说出原因,但精神上的不适是超出理性的。
苦难不过是时间手中无情圣剑的一击,它分开了意义与虚无。然而,我还是强迫自己努力给出一个解释。在我看来,有时他深邃的双眸有着令人无颜面对的坦荡。它们似乎对我们文明时代的算计和猜疑过于轻信,过于单纯。因为当我感到安逸自在时,它们似乎就对我和这个世界抱有指责(虽然我从不确定我弟弟的个人情绪和意图)。
我希望,我可以更坚定地处理这些细微的不适,但我做不到。我只知道,它一开始就在那里,从我记事起,它时不时地以一种无意识的恼怒表现出来。不管多么不合理,不公平,不管我采取了怎样与此相反的措施,它总会从我身上不耐烦地爆发出来。
更糟的是,我弟弟似乎从未介意。他十分自然地接受这一切,几乎把它当做自己黝黑的皮肤和不可剥夺的出生权的一部分。当我像一直以来做的那样笨拙地乞求他的原谅,他会亲切地看着我,语速很快地说:“但这不算什么,哥哥,这有什么,别放在心上。”事实上,他的举动会表现得好像我刚刚帮了他什么大忙,好像正是我的极度不耐和气恼给我们俩一个本来绝对不会存在的机会。
这一切都难以说明,我不得不让自己通过接受它是某些不可避免的事而平静下来。但是,我怀疑生命给我造成的缺陷(如果这算是缺陷的话)也融入了我们所有人之间最大种子的存在和生根发芽中,就像最初在贝壳中孕育珍珠的那个极小的瑕疵那样。
有人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比为朋友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伟大的爱了。”然而,一个人为他的敌人而活,助长他们对他的敌意,这也许不是一种伟大的爱。直到他最后的敌人有了足够的恨意前,他永远不会成为自己敌人。他的敌人将自由地发觉他们可怕饥饿的真正含义——就像我弟弟激起了我奇怪的敌意并忍受着,但他从没对我怀有敌意那样?
然而,我不是爱的专家,而是背叛的专家。我没有资格代表专家发表意见。就像我弟弟代表我一样,我不会过分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我讲述故事的比例起见,我必须多说一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对我弟弟有这种反应。他对绝大多数与他经常接触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影响。
我说过,我变得高大优雅。他从一个又矮又胖,身材笨重的人,变得更壮更重,他的动作显得笨拙。我怕他长得并不好看。他的魔力在他的眼睛里,不幸的是,它们让人不适。他的头甚至比宽阔的肩膀还大,然而与他粗犷的躯体相比,他的脸有着令人窘迫的温柔。他的额头从出生起就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中间是双冠状的头发。结果,这看起来是一张深沉且乌黑的脸。当他笑起来,露出他的一口白牙时,这张脸就会变得惊人地明亮,甚至说是美丽。但遗憾的是,他很少在公众场合笑。当我们俩紧张的关系得以缓和时,他似乎为我们俩保留了笑声。所以,通常情况下,他的脸并不舒展,沉思着自己的天性,就像一只黑色的非洲母鸡沉思自己的窝一样,头微微昂起,对我们炎炎夏日里太阳所拨动的光之竖琴的乐声充耳不闻,只听着她内心对生命的充满激动的期望。
在学校里,我从玩到学的大多数事情上,表现都很出色。我弟弟只能勉强通过考试,体育方面他不感兴趣,也毫无技巧。我跑得很快,是一流的短跑者;他行动迟缓,是一个不知疲倦,蹒跚前行的散步人。我爱动物,喜欢非洲焰火闪烁的游戏和太阳火鸟。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但他从幼时起就被地球上所生长的一切吸引。我没有耐心去搞种植,他却喜欢犁地和播种。
令人惊讶的是,他粗苯的手指是如此成功:无论他把什么东西放进土里,似乎都会生长开花。他常常跟在他最喜欢的一群紫色杂毛公牛的后面,从晨光熹微行至晚霞渐残。他有着厚重的刃的单铧犁将非洲深红色的大地翻成波浪状,宛如荷马时代的一艘柚木船的船头,在清晨酒红色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在一天的深耕晒垡之后,他于暮时归家。我总能看到他安静地坐在犁柄上休息。
“你在琢磨什么呢,小弟弟” 我总是这样和他打招呼。
注:图片源自网络
X 关闭
- 《种子与播种者》原著全文翻译【第9期】
- 前妻因为宫颈癌去世,如今第二任妻子又查出宫颈癌!医生:可能和丈夫有关_世界快播报
- 步话机简介(步话机)
- 当前资讯!头显减产?苹果投石问路
- 世界今亮点!antszone蚁族男装死掉了吗_antszone
- 环球热点评!德国投资外流趋势难遏
- 林雪萍|你想造芯片,美国人想缝衣服_世界看点
- 宝利通HDX7001_关于宝利通HDX7001介绍
- 最佳新秀排第二打夏联!杰威:我爱打球 终于不用只和助教对抗了 资讯推荐
- 张同学爆火的真相_张同学爆火东北人 全球快看
- 好消息!东丽区这个老小区的充电桩能用啦!
- 浙江:亚运测试赛激战正酣 老场馆焕发新活力-天天观点
- 当前热点-昊志机电:公司生产的谐波减速器等产品尚未应用于人型机器人领域
- 毕业证样本淄博(毕业证样本) 环球速读
- 太原列车时刻表查询最新(太原列车时刻表)|环球今日报
- 突出党建引领 株洲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千名干部进小区”活动
- 2070亿!欧盟公布涉俄这一数据|最新消息
- 美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使北美鸟类繁殖力下降 世界头条
- 焦点报道:万宁文旅踏浪前行
- 云南昭通多地遭受暴雨袭击 紧急转移8350余人
- 天天新动态:心理小测试 测试一下你最缺少哪种能量?
- 短讯!蔡自力已任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
- 天天要闻:秘密吸引力法则成功案例(如何真正理解秘密这本书中的吸引力法则)
- 湘雅常德医院2名护士火车站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我们天天在做”_全球独家
- 热推荐:美国制造业活动创出三年来最大降幅 连续第八个月萎缩
- 天天滚动:发票号码和机打号码不一样怎么办(发票号码和机打号码不一致怎么办)
- 湖北大冶:大步迈向科创之城_世界百事通
- 昼夜鏖战织“天网”!陆军某旅携手空军某部开展对抗演练-世界播资讯
- 数读中国 | 五组数据速览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新格局_全球热点
- 世界看热讯:*ST三盛7月4日快速上涨
- 商业承兑贴现网_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网
- 东北地区今明天强降雨来袭 华北高温短暂休整后将再发力 天天微动态
- 流金科技:7月3日获融资买入19.61万元
- 【时快讯】ETF半年成绩单出炉,非货产品首尾业绩差达115%
- 全球即时:车载gps定位仪安装在哪里_车载gps定位仪
- 环球热资讯!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2023年三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 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探底恢复
- 全球微速讯:7月3日基金净值:工银成长精选混合A最新净值0.7329,跌1.11%
- 实时焦点:营养减肥餐厅_营养减肥餐
- 今日要闻!美农超预期下调种植面积和季度库存报告,7月豆粕期价“喜提”涨停板
- 天天快报!经典老版qq提示音_经典老版qq提示音噔噔噔
- 连续两天成都蓉城队都有好消息传出_热点
- 公司是否有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桩技术储备?铭利达回应-今日最新
- 共赴鸿蒙是什么意思(共赴鸿蒙释义)
- 世界观察:龙虎榜丨巨轮智能获4亿资金抢筹,机构净买入额超3.4亿(名单)
- 环球视点!京东信阳黄国云仓开仓仪式举行
- 手机如何下载qq浏览器(手机如何下载qq)
- 世界今头条!复旦大学:今年在河南招生164人,招生组联系方式来啦!
- 拿得下来英媒:波切蒂诺向董事会提出签下凯恩,助蓝军争夺冠军_天天动态
- 闽清雄江片区基础设施加快建设_世界视点
- 环球精选!2023南通通州区幼儿园招聘教师报名时间+入口
- 贝莱德基金副总经理张鹏军离任_环球观点
- 天天速读:超可靠智慧性能SUV再升级,AITO问界M5标准版正式亮相
- 黄子韬进入狗仔爆料直播间 在线吃瓜蔡徐坤
- 每日快讯!日本开售方形西瓜:不能吃只能观赏 每只卖500元
- 全球时讯:the beatles经典歌曲合集完整版_the beatles经典歌曲
- 小米12什么时候上市的(小米六什么时候上市的)
- UTS MARKETING:Exsim已承诺于2024年7月1日或之前偿还贷款
- 她没有手指,但字迹工整清秀!高考超过一本线6分..._热头条
- 2022全年OPPO共获2875件专利授权 位列国内企业第四
- 我国首艘数字孪生智能科研试验船“海豚1”号烟台交付并首航
- 医药股早盘多数走高,长春高新涨近5%,创新药ETF(159992)、港股通医药ETF(159776)双双飘红丨ETF观察 世界热议
- 《长风渡》:看懂周高朗任由周烨在帐前长跪,才知他根本不信顾九思-快看
- 灌篮高手全国大赛漫画解说40 灌篮高手全国大赛篇图文解说
- 资讯推荐:中国奥园2022年总营业额约187.11亿元 同比下降62.6%
- @准大学生,高效准确填报志愿,要做好这些“功课”
- 【世界独家】建党节 |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 骄傲!夺冠!昆明超强姐妹花“顶峰相见”
- 海南需要什么样的导游?
- 安徽安徽公摊面积动迁如何赔偿?_世界新要闻
- 安微省_安微 当前报道
- 艾滋病检测的最佳时间2022年_艾滋病检测的最佳时间
- 最新:定州石佛寺遗址
- 中国篮球协发贺信:祝贺中国女篮时隔12年再次登顶亚洲之巅! 环球看热讯
- 河北封闭式学校有哪些 河北有哪些封闭式学校-世界今日报
- 铁道飞虎每个人简介 看龙叔一路走来 全球看热讯
- 青少年纠正学校 孩子去青少年纠正学校有用吗
- 年销量160万 冲击豪华品牌第一 是增程式给理想的自信?
- 宁武关_宁武关之战相关内容简介介绍
- 世界时讯:羊肉汤胡椒粉配方?
- 黑暗侵袭三部剧情_黑暗侵袭3剧情详细解析
- 火锅店开店调研,望江门火锅加盟是哪里的?做到了信息共享!
- 佩德罗卢卡斯(卢卡斯佩雷斯马丁内斯)
- 法内政部:警方继续逮捕骚乱者,目前被捕者平均年龄17岁|今日视点
- 全球快播:环保dbp是什么意思(dbp是什么意思)
- 男子外出干活遇超大菌子 世界速看
- 法治日报:父母子女共同购房,产权归属如何认定?
- 天天观速讯丨Here we go×2!罗马诺:索博斯洛伊通过利物浦体检,并已签署合同
- 临邑怎么读_临沂怎么读
- 关于封神的11年
- 天天播报:盘点Pandas中数据删除drop函数的一个细节用法
- 江苏省2023年普通高考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将于7月2日17:00截止-环球报道
- 【天天播资讯】JDG不加班,零封UP!评论:宁王状态渐好,可惜蕉太狼道心破碎!
- 世界视点!鸡油菌科_关于鸡油菌科简述
- r是什么数学符号_r是什么数
- 萌娃左手敬礼给警察叔叔整不会了
- 云南干部要有什么特质?省委书记:树立“十种鲜明导向”! 天天热推荐
- 贵溪官方通报:系硅油着火引发火情_全球讯息
- 高中化学!48个重点难精编!
- 2023年7月1日正辛醇价格最新行情预测 天天最新
- 【世界热闻】脱不花: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Copyright © 2015-2022 时代商报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 联系邮箱: 514 676 113@qq.com